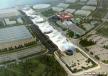2003宏观经济年中分析:四因素促投资高速增长
2010-08-26 15:38:57 来源:上海证券报
看法
■由于市场周期、资金来源、外贸出口、金融支持等多种有利因素抵消了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疫情的负面影响,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加速增长态势。一批市场化程度高、对政府直接投资依赖性小的行业投资增速大大加快,说明由新一轮经济扩张周期带动的企业自主投资机制正在形成。
■随着规模的迅速扩张,我国投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更新改造投资超过基本建设投资;第二产业增长强劲,第一、三产业增长偏慢。产业结构"冷热不均"问题比较突出,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当前投资政策的主基调应是:适当控制投资率的不断上升,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同时还应采取措施大力刺激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形成以消费增长带动投资,以投资结构优化提升消费水平的良性互动增长机制。
固定资产投资何以迅猛增长
上半年,伊拉克战争导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非典疫情对我国及东亚地区带来负面影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非典疫情的影响下,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出乎预料"地加速增长,成为抵御"两大冲击"和推动GDP高增长的主要力量。据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578亿元,同比增长31.7%,高于去年同期5.9个百分点,是1994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增速。我们认为,投资迅猛增长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进的。
1、市场周期因素
首先,经济运行进入新一轮景气扩张周期,是投资高增长的根本因素。去年以来,受多年积极财政政策效应集中释放和入世等利好因素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进入了新一轮景气扩张周期,GDP增长逐季加快。这不仅为投资提供了充裕资金和物质条件,而且也为投资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和空间。同时,它也使企业家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大大增强了企业投资意愿,投资信心指数大幅上升(一季度为108.2),达到近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其次,消费结构升级大大拓展了投资的领域。二十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和有关刺激消费措施的出台,住房、汽车、电讯、娱乐等成为人们消费的新热点,不仅加快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而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房地产、汽车以及电子通讯等相关产业投资的迅猛增长。以房地产为例,由于住房消费热不断升温,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持续高于全社会投资水平。同样,汽车已经成为城市消费的新时尚(近两年表现得更加突出),有力地带动了汽车以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增长。消费结构升级不仅引导房地产、汽车、旅游、消费类电子等行业投资增速不减,同时也掀起了新一轮机电、化工、冶金、建材、交通运输、电力等一大批相关产业的投资热潮,大大拓展了投资的领域和空间。
此外,近几年政府投入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城市化形成了积极的推动。我国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19.0%提高到2002年的37.3%。城市化进程加快带动了投资需求的增加,是投资快速增长的又一重要动力源。同时,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也向民间资本和外资开放,投资来源不断拓宽。
2、资金来源因素
充裕的资金来源,是投资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今年投资资金来源充足,有力地支持了投资高增长。前5个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累计到位资金13443亿元,同比增长46.3%,比去年同期提高14.6个百分点。同时,在总投资增量中资金来源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预算内资金在总投资增量中的比重明显下降(由1998年的14%下降到2003年5月的4.9%),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所占比重迅速上升(由1998年的85%左右上升到2003年5月的89.7%)。这说明影响投资增长的动力机制中,政策性因素在不断减弱,市场周期因素在不断提高;投资自主增长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对提升投资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国的投资增长格局,已经开始由政策推动为主向市场推动为主的方向转变。
3、外贸外资因素
虽然伊战前后的不确定性使石油价格一路攀升,打击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但美国、日本、欧盟三大经济体在战争阴云笼罩下依然缓慢回升(一季度分别增长1.9%、0.01%和0.8%)。另外,俄罗斯、东欧、印度等国家经济增势强劲。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美元贬值以及我国入世效应的继续发挥,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非典对外贸的影响。上半年我国外贸形势依然喜人,出口增速继续保持高位(前5个月增幅达到34.4%,加快21.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外向性进一步增强,为拉动投资需求产生了重要作用。
4、金融与政策因素
第一,金融机构注入的资金大幅度增加。今年5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20.2%,增幅较去年同期加快8.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增长18.8%,加快4.2个百分点。各项贷款自去年8月份以来,持续大幅增加。去年新增加的1.8万亿元的贷款中,有近1万亿元是8月份以后投放的。今年1季度,新增各项贷款18003亿元,同比多增加7663亿元。
第二,体制性因素的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但是,投资领域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没有真正改变,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对投资活动介入太深。为了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充分体现工作政绩,一些地方政府总是把投资作为重中之重。有的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依靠大规模出让土地、收取50至70年的土地出让金来补充财力,扩大投资。有的地方政府大搞开发区,纷纷兴建汽车城、大学城、电子城、工业园等,一大批建设项目正在筹划或建设之中。今年是新一届政府运作的第一年,投资增长自然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和工作重心。这也是当前投资增长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之一。
总量在扩张 结构不均衡
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当投资总量扩大时,容易形成较为合理的投资结构。因为投资总量供应充足,有条件满足各地区、各产业、各种项目等多方面的投资需求,使投资结构相对均衡、合理。从今年我国投资增长的实际看,随着投资总量的扩张,投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一些变化改进和优化了投资结构,但有些变化则使原来存在的投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
1、投资运用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更新改造投资增长大幅上升,超过基本建设投资增长
在市场预期好转、上年基数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下,今年上半年技术改造投资实现了近年来少有的高增长势头,改变了2001年以来技术改造投资增长偏慢的格局。1至5月份,更新改造投资完成1994亿元,同比增长37%,比去年同期提高近20个百分点,而且高出同期投资增幅5.3个百分点。更新改造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由去年5月的17.9%上升到今年同期的18.9%,上升了1个百分点。与技术改造投资高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基本建设投资增势平稳。前5个月,基本建设投资完成5352.9亿元,同比增长28.7%,占整个投资的比重由上年的51.4%下降到今年的50.6%。技改投资增幅超过基本建设投资,是今年投资领域出现的一大突出特点。这说明,一方面我国投资开始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变;另一方面,与以往固定资产投资不同,设备投资明显增加,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更新的周期已经来临,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因素正在不断增强。
2、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增长强劲,第一、三产业增长明显回落,投资的产业结构"冷热不均"问题突出
今年投资结构上最突出的问题不是以往地区之间的矛盾,而是产业之间的矛盾:第二产业投资热度不减,而第一、三次产业投资增长缓慢,同时第二产业内部不平衡问题有所突现。
第一产业投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投资。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阶段,第一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是合理的,但这种下降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我国目前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与增加值反差较大,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过高,说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今年前5个月第一产业投资增长仅为12.4%,比去年同期回落17.6个百分点,农业投资在整个投资中所占比重,也由去年5月的3.4%下降到今年同期的2.9%。这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农村人口比重不相协调,也与解决农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等要求相去甚远。
第三产业投资总体规模继续扩大,但增幅明显下降,在整个投资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今年前5个月,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8%,低于上年同期2.9个百分点,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由去年5月的65.7%下降到今年的61.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产业内部,投资结构的变化与非典疫情息息相关。受非典打击比较严重的商业饮食供销仓储业、房地产公用服务业投资增幅明显回落,由去年的增长23.5%和35.5%分别下降到今年的8.0%和28.5%。同期与防治非典有关的文教卫生广播福利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投资增幅分别提高了13.4和84.4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增长速度较快,传统工业投资出现"爆发式"增长。今年前5个月,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7%,增幅高于去年同期27.5个百分点。随着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基础行业投资快速增长,煤炭、冶金、有色、化工、机械等增长幅度都在58.1%至141%之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市场化程度高、对政府直接投资依赖性小的行业投资增速大大加快,说明由新一轮经济扩张周期带动的企业自主投资机制正在形成。但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矛盾重现。主要是前几年能源工业投资缓慢与新一轮加工工业的增长不协调,同时高能耗行业增长偏快,一般加工能力产能扩张过快,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升级类投资比重偏低等。
投资率过高令人关注
随着投资增长持续高位,有关我国投资率是否过高再次成为当前管理层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上使用的投资率指标在口径上大体有三种,但常用的计算方式是: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100%。根据这一公式,我国1984年至1988年的投资率约为31%,1992年至1996年为35%,1998年以来都在35%以上,去年达到39%,今年上半年估计突破40%。可见,不管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投资率已经存在偏高的问题。
投资率过高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一定时期的高投资率固然有助于加速经济发展,但已有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成长的拉动是以有效投资为前提的。如果投资没有效率,投资过度,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没有跟上,反而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从我国经济发展来看,投资率过高,不仅使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而且导致回报率过低,影响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因此,在投资增长加快、投资率一路走高时,要密切关注投资效率以及投资与需求的结合程度。
与投资率居高不下相伴的是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不断下降。2002年我国消费率为58.2%,比"六五"时期的66.1%低7.9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消费率约在80%左右。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2002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1000美元,但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却仅为48%,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3个百分点。消费率过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执笔:周景彤)
总体策划
王长胜(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张伟弟(上海证券报副总编辑)
课题负责人
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
赵嘉国(上海证券报编辑部主任)
课题组成员
邹民生、张学颖、祝宝良、王远鸿、陈明星、胡少维、伞锋、祁京梅、张峰、王硕、朱明、李若愚、周景彤、董月鲜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